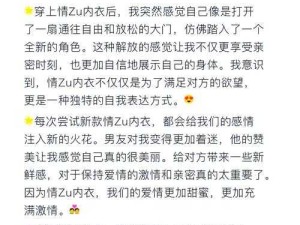男女被=$流到爽 ovenight:禁忌之河的迷雾秘事
夏末的国道像条煎熟的蛇。阿城扛着登山包在柏油路上独行时,看见路边蜷缩着个人影。像是某种野生动物误入人类领地,慌乱地把脸埋进双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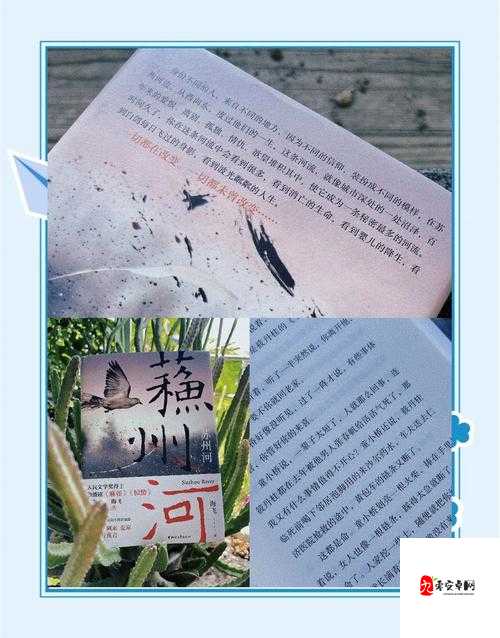
雾气在前一秒才出现。先是灰蒙蒙的颗粒悬在公路边缘,转眼间就凝成一团浓稠水汽。那姑娘就在这团雾里,像被某种无形力量扯着衣角往后拽。阿城看见她张嘴想呼救,气流却化作袅袅白烟消散在空中。
"喂!你他妈在哪鬼叫!"他抄起登山杖冲进雾里。手臂刚触到冰凉雾气,突然被一股隐力拽得弯下腰。那雾像活物般纠缠着他的喉骨,指尖能摸到绵软的触感,却看不见半点实体。
终于在草丛后找到挣扎的身影。姑娘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衣领处渗着暗红色血珠——有人薅她衣领的力道,跟拔萝卜似的。阿城抄起背包里的登山绳,三两下就把两人拴在路边铁丝网架上。刚系好第三个活结,雾气突然沸腾般炸开。
"这是茅家渡的鬼水。"姑娘凑近他耳边,温热的呼吸拂过耳垂,"每年总有几个不知死活的闯进来。待会儿你会看见不该看的,听见不该听的。"
鬼水里的浮世绘
铁丝网后的雾境像被搅乱的糖浆,剥开层层包裹露出底下翻涌的景象。先是飘过几串荧光串灯,悬在半空中画着莫可名状的轨迹。接着看见断桥残垣在雾里若隐若现,桥堍立着块风化严重的石碑,依稀认得"民国二十年"几个字。
远处传来咏叹调式的唱腔。歌词是半文半白的怪调,像被钝器捶打的古琴声托着:"合欢树下深沟泥,磷火灯笼寻渡期。要入迷津还得去,皮囊换过重相惜。"
姑娘突然抓住阿城的衣袖,指甲掐得他骨头肉疼:"看那边!"顺着目光望去,雾里浮着几截赤裸肢体,像是从不同人身上掰下来的骨骸。男性的手臂泛着古铜色腱子肉,女性小腿却裹着袜跟鞋——两具肢体在空中拼接重组,形成某种诡异的变形生物。
渡河人的诡戏
当他们缩在铁丝网后颤抖时,雾里钻出辆摩洛哥风情的三轮车。车手戴着阔檐礼帽,兜帽里垂下的丝绒发带随着呼吸微微颤动。后座绑着个黑色网兜,里面蜷缩着看来比阿城还高的壮汉,却像即将融化的雪人般不停渗出半透明液态。
"哟,又来两匹生血马。"车手冲着壮汉的方向啧啧两声,转脸对阿城笑:"现在改规矩了。今晚来观光的,每人交三枚硬币,外加这条登山绳子。"
阿城还没来得及反对,姑娘突然掏出叠得方正的二十五元纸币塞进口袋:"生死有命,钱总要留着买棺材。"说着冲进鬼雾里,阿城看见她的影子在雾里碎成碎片,像被碾过的玻璃窗纸。
一夜漂泊的代价
当黎明把雾气驱散,茅家渡的景色让阿城想起清晨五点半的集市水产批发区。岸边横亘着三十多具半裸尸体,整齐得像超市货架上的冻鸡。每个人咽喉处都嵌着枚铜板,正面铸着枚古钱纹样,背面刻着陌生的阿拉伯数字。
他摸着僵硬发凉的后颈,突然想起三轮车车手的话。那枚嵌入他皮肉的铜板,此刻正嵌着某种微弱的电流,像是老式收录机的针头始终在耳膜上划出尖叫。
这时头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响。抬头看见姑娘骑着辆蓝色摩拜,车筐里晃晃悠悠吊着他的登山包。她说这些铜板会在第七天凌晨三点熔化,直到那时候,阿城每晚得把自己泡在自来水里七七四十九次。
"不过这把骨头挺值钱的。"她踩着变速把手冲他笑,不知是雾气还是晨露让睫毛挂满水珠,"明晚这时候,沼泽街二十号等我。"
三轮车的铃铛声在雾气里消散。阿城看着姑娘骑行的背影,突然想起那个诡异的镜像——在雾里浮现的尸体,和后座被绑着的壮汉,五官都依稀带着姑娘的影子。
永不止歇的轮回
七日后的沼泽街20号透着鱼市晨间的腐腥气。推开门撞见三轮车车手正用果汁机搅碎某物,浆液里沉淀着细碎指节。墙上贴满历年打折券和街区示意图,最显眼的位置悬着枚发黑的铜板——正面还是古钱纹样,背面的阿拉伯数字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写。
"欢迎来到永不打烊的转会市场。"车手朝他递过枚铜板,新鲜得连余温都未散尽,"这玩意儿能换三套房子首付,但你得先把眼眶里的窗纸撕掉。"
姑娘正蜷缩在二手冰柜上嗑瓜子,听见这话突然把整把瓜子塞进阿城口袋。他摸到冰凉的触感,突然意识到那包瓜子壳里藏着半张医院验血单——上面的血型,跟岸边三十多具尸体完全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