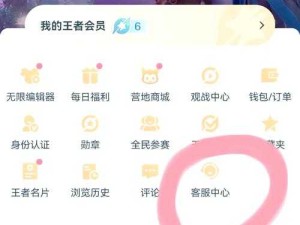禁忌之触:当胸罩滑落的瞬间引爆欲望
夏末的雨总爱这样突然。我倚在老旧弄堂的铁门框上,看着豆大的水珠子砸在油光发亮的水泥地上。对面二楼晾着花棉被,水渍浸润出一片晕染的海棠色,活像去年戏台子上演玉堂春时筱燕秋贴的那张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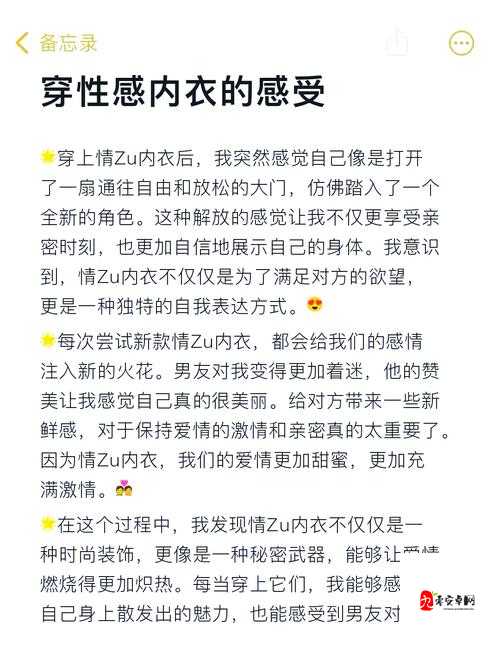
她就从那花棉被的窗子里探出头来,冲楼下洗菜的中年妇女喊:"老李!借把剪刀!"声音里裹着股子裹脚布似的黏乎劲儿。那妇人应着往墙根探身,半截蓝花布衫子也不自觉地往腰后甩,露出背后印着白蛇传的红底褥子。
雨一下就停了。阳光像是从蒸笼里捅出的热气,顺着屋檐的水珠往下淌。我看见她赤着脚踩过水洼,脚趾头挤成朵喇叭花,鞋面上还沾着墨绿的藓。她路过我身边时总算察觉了,往后趔趄半步,兜里的橘子滚出来,在水滩里轱辘轱辘转。
这下她可慌了。先是蹲下去捞橘子,手指尖戳进泥水里,接着腰带上的铜纽扣"咔嗒"掉进下水道。她使出吃奶的力气扒拉窗台,裙摆就这么往后扬,露出月白色真丝内里。我听见门闩转动的声响,好像有谁正要把这只飞起的蝴蝶钉在墙上。
"要不要帮个忙?"我的话还没说完,她已转身抄起竹竿,劈头盖脸抽来。那竹青色的影子划过空气,带着果园老窖似的闷香。她说不准碰她,可手心里攥着根生锈的钢锯条,在雨后潮湿的砖墙上划出道道血痕。
天擦黑时厨房飘来醋烧鲤鱼的味道。我蜷在阳台上抽烟,烟圈总爱往对面窗子里钻。忽然咔嗒一声,窗子支棱开条缝,投出块青砖大的方形月光。她的胸罩就这样悬在半空,白色蕾丝爬满红尘,像朵永远开不了的曼陀罗。我冲上去拽她时,整个人都栽进那方月光里。
暖烘烘的触感比隔夜茶还叫人犯晕。她浑身裹着煮过的痱子粉味,却比先前在梨花树下摘果子时凶了十倍。指甲掐得后背殷红,可那枚铜纽扣始终硌在肚脐眼下,刺得我脑子里只有雨丝样的钝疼。
隔天巷口修鞋摊的老王头非要请我喝酒。他说前两天遇见个穿红裤子的姑娘,说是来寻夫家。酒斟到第五巡时我才明白,那女人的胸罩已在第三天清晨飘进下水道——和那枚铜纽扣一起。
雨又下了起来。这次下的不是七月的瓢泼,而是八月里的缠绵。对面窗台晃动的烛影里,我看见那红裤子姑娘正给谁扣衣扣。她的手指绕着按钮转三圈才肯放手,就像是绕着那枚永远找不回来的铜纽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