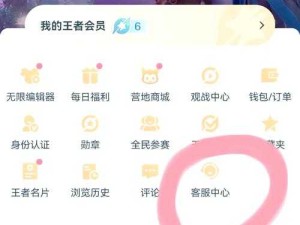光腚驯服!野性与征服的终极挑战
那片原始雨林像个贪婪的吸血鬼。枝叶纠结成网,吞没了最后一线天光,潮湿的雾气从地面渗上来,裹住裤腿,像无数条冰凉的手指试探皮肤。我正蹲在洼地摆弄相机,突然听见后颈根子炸裂似的响——一柄猎刀架在脖子上,带着铁锈味的呼吸贴着耳垂滑过去。

"交出相机。"
声音粗粝得像被砂纸打磨过,混着某种原始的野性。我僵在原地,这人抓我手腕时我才发现,他连件完整衣裳都没穿。午后的阳光从树冠漏下来,在他腰间的野藤间跳跃,皮鞭扣着水珠,在地上拉出一条湿漉漉的纹路。
(一)荆棘与欲望的开端
他自称是这片山林的主。第二天我被他带到断崖下,那里扎着圈竹篱,篱笆尖上插满倒生的荆棘。我问他这是作甚,他笑得露出两颗虎牙:"驯野马还得用铁丝。"
他把我的手腕绑在篱笆柱上时,我看见他袖管卷到小臂,青筋在皮肤下拱动。日头毒得很,汗水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淌,打湿后腰一片。他拿了根藤条,一圈圈裹我的脚踝,动作粗暴得像在捆杀猪的。
"喊疼也没用。"他说,"你是匹不听话的马。"
那日过后,我的屁股印了三道血痕。夜深了他却让我跪在火堆旁,拿温酒洗伤口。我缩着腿想躲,他却按住后脑勺,酒水顺着脊背流下来,烫得我打哆嗦。他没头没脑丢句:"你这皮也太嫩了。"
(二)皮鞭下的征服仪式
他开始教我用野果充饥。第四个黄昏,我在山坳里摘到拳头大的树莓,汁水染红了手心。他眼眶发赤,抓过果子塞进我嘴里,手指还沾着树莓汁的痕迹。
"慢慢咽,"他说,"连籽儿都要吞下去。"
这成了某种隐喻。他总在雨天把我推到瀑布前,皮鞭抽在身上时水雾滚烫,像有人在皮肉上浇滚油。有一次我晕倒在青石板上,醒来时他正拿布条蘸山泉水擦后背。他骨节分明的手指捏着我脊椎,力度刚好让我喘不过气。
"痛快是吧?"他凑到耳边,舌尖扫过耳垂,"你这皮肉就是我的土地。"
雨季结束那晚,我在松树窠里发现了狐狸的骨骸。白森森的骨架还裹着腐肉,我想起他说过的话:"野兽最怕铁器。"
(三)丛林中的权力游戏
第七个月遇见猎豹时,我们都在趟沼泽地。他朝我怀里塞了把猎刀,却没来得及告诉我刀柄藏着锈斑。我拔刀的动作太快,虎口被划开道口子,血珠子往下滴时,树叶深处传来低沉的兽吼。
猎豹是跑得最快的野兽。它扑过来时我看见森绿的眼瞳里倒映着腥红——那是他身后的月亮花开了。他这时才亮出带倒钩的甩棍,金属碰撞声惊得我也忘了躲。刀尖插进豹子胸口时,鲜血溅在我光着的大腿上,温热的触感让我想起刀茧子抽完后的麻意。
他蹲下来替我包扎伤口,忽然抓住我后颈往后扳:"知道你最怕的是什么吗?"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,他就吻住了我耳后根子那道刀疤。
(四)光腚征服者的荒诞仪式
某个落叶红如火的晨光里,他突然让我脱光上衣。我问他这是要搞甚幺把戏,他眼神变冷:"看看你这皮肉还有没有野性。"
我们在山桃花雨里滚了整整一天。他把皮鞭绕上树桠,把我吊在半空,我能听见皮肉摩擦树枝的沙沙声。他总在这时候说起山外事,像说跟泥地石头似的闲话:"那些穿西装的,在写字楼里流汗的样子,比不得你这儿根鞭子抽出来的快意。"
深秋的晨露落在我肩胛上时,我看见他腰间别着把微型摄像机。镜头对着我满是伤痕的后背,他按快门的声响惊飞了树梢的乌鸫。
"这是证据。"他这么说着,从口袋里摸出第二块硬盘,指节因为握得太紧泛白,"现在这野性,都是你给我的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