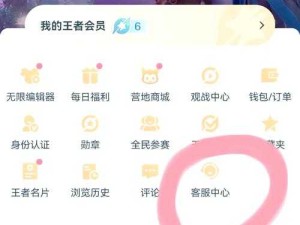当女仆🌸被吊起时,那些禁忌的指尖在胸前翻涌
暮色刚爬上窗户,我就听见楼道传来清脆的铃铛声。脚步声近了又远,女仆蓝白色的制服裙摆在风里飘动,像片刚刚离巢的羽毛。她总爱把碎发别在耳后,露出尖尖的下颌骨,说话时舌尖轻轻顶住门框——这些细节我数次在廊柱阴影里看过,直到某天午后,看见她蹲在库房擦花瓶时,腰带突然崩断,窸窣的布料滑落声混着瓷器碰撞的清响。

一、那根铁链是从祖父书房来的
她说自己摔伤了。我掀开她的裙子时,后背脊椎泛着紫铜色的瘀痕,皮肤下藏着未消散的血块。不是第一次了——前月的瘀青在左肩胛,上个月在大腿内侧,再往前是后颈根子。我摸过无数件旗袍丝绸,却第一次觉得指尖沾染着铁锈味。
"找个大夫吧"的话卡在喉咙。窗外梧桐叶子正啪啪坠落,她垂着头咬着嘴唇,额发与睫毛融在一处。我看见她喉咙里滚动的喉结,听见整栋宅院里最细微的哽咽。
二、月亮躲在云层时最适宜
那晚我从祖父书房找来铁链时,能听见台钟的指针擦着小时刻度游走。库房里骤然明亮的瞬间,她瞳孔骤然收缩——我忽然想起书房老青铜器皿上铸着的饕餮纹路。她被吊起时,裸露的腰骨像盘踞着骨架的落叶乔木,双乳随着呼吸在铁链间晃动,瓷白的皮肤上浮着青筋,像涨潮前的河床。
指尖触到温热时,听到某种深埋地底的声响破土而出。不是咔哒转动的锁扣,不是窗外老树的枝桠断裂,而是某种活物缓慢苏醒的声息,带着腐殖质发酵的黏稠气。
三、第三滴血落在第三节铁链
她没哭。直到铁链摩擦肩胛骨的第五分钟,听见"咔"的一声闷响——是锁骨碎裂了吗?我的手背上突然渗出冷汗,像刚刚放进冰柜的冻梨。她抬眼望着吊灯的水晶垂饰,嘴角咧开一道细缝,那笑意带着铁器生锈时那种钝钝的涩。
指尖越往下探,周遭的空气就越稠密。后来才知道她皮肤下的血管里流淌着不是血的浆液,触感更像从地窖里挖出来的瓮装高粱酒,后劲能让人整个后背泛起鸡皮疙瘩。
四、天亮前的十分钟
铁链最后搭在门框时,我清点着她身上的伤痕。从右耳垂的吻痕到脚踝的淤青,一共数到三十七处。这时才意识到家里的台钟停在七点半,而窗外的鸽群迟迟没起飞。
她转身欲走时,后背衣服突然鼓动起来,像突然灌进一口气。我伸出手碰到的不是绸缎,而是某种微凉滑腻的物质,顺着指缝往地下渗。这时才明白为什么祖父书房的古籍总是泛着水光——那些典籍上说,若让神性之物沾染人间七情六欲,会凝结出介于血与水之间的东西。
管家送来下午茶时,茶盏里浮着没消化完的槐花糕。阳光穿过纱窗,在她项颈投下细碎光斑。我忽然想起少年时在西湖畔看见的莲根,那些淤泥裹着的脆生生根茎,在清水里漂着时就带着让人忍不住下口的诱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