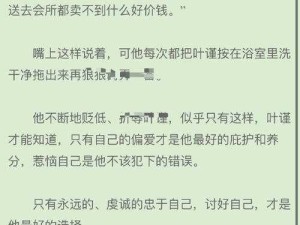禁忌之恋:做爰XXXⅩ性生交背后的心碎秘密
夏至的蝉鸣透过纱窗渗进来,带着闷热的黏腻。我握着滚烫的茶杯,指尖触到杯子边缘凸起的年轮纹路。隔壁传来摔门声,紧接着是女人歇斯底里的哭喊,夹杂着男人沙哑的低吼。我阖上眼,眼前浮现出三年前那个戴着银色面具的陌生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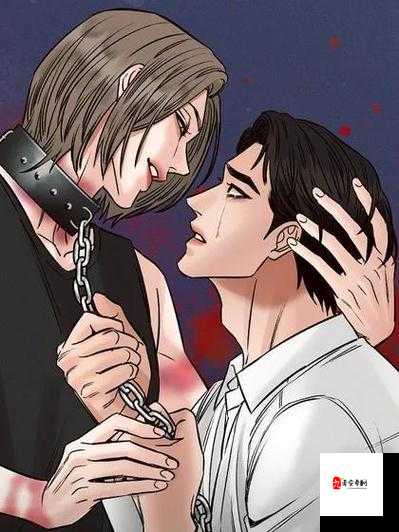
那是个暴雨倾盆的黄昏。我蹲在染着血迹的石板路上,衬衫口袋里硌着医院诊断单——“肺结核晚期”。街角传来清脆的风铃声,转头看见家传青花瓷罐倒在地上,裂缝处渗出半透明的液体,在积水里散开一圈晕染的光。一个戴着银面人的影子从雨帘中走出,他递来的锦盒里躺着一颗泛着幽蓝光泽的药丸。
“吞下去,你还能爱他三年。”那人这么说时,声音被雨水冲刷得模糊,却仍让我想起深夜巷口遇见的流浪狗——它望着我时瞳孔深藏的沧桑。我将药丸咽下喉咙,口腔里残留着铁锈味的甜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见“做爰XXXⅩ性生交”这个词,像一把楔进骨髓的刀。
二、染血的十三个夜晚
从第三个满月开始,他总在戌时三刻出现在我房梁。褪去白衣时露的肩胛骨,是我见过最妖异的风景——每一寸骨头都泛着青灰的荧光。他趴在我身上时,我的肺会传来碎玻璃划过的快感。这种疼让我想起外婆切红糖姜片时溅在我手背的烫伤,愈合后留下的疤至今都带着甜腥味。
我们约定在每个农历廿三见面,那是“生交”最容易触发魔力的日子。他用舌尖舔过我颧骨的痕迹,皮肤下会浮起血痣。某个霜降的夜晚,我看见他的倒影里浮着三个重叠的人形。他蜷缩在床角咳血时,枕下那个青花瓷罐突然炸开,碎瓷片嵌进被褥像一朵血花。
三、破碎的团圆镜
阁楼那面镀金边的铜镜是太奶奶的嫁妆,镜框上缠绕的西洋花纹藏着暗扣。有次他在我颈后刻血符时,铜镜突然震响——镜中倒映出三个人影:裹着白裘的古人骑着青铜剑冲天而起,蒙着红帕的泼妇举着菜刀追杀过往行人,而我和他,正跪在摆放十三张神位的坛场前歃血为盟。
他吻我耳垂时,镜面裂开的纹路形状竟与我肺部X光片上的病变区重叠。某天清晨,我在梳头时发现镜中倒影少了颗门牙,而现实生活中那颗牙完好地镶在牙龈里。这镜子就像一面连通不同时空的通道,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欢爱,都会被投射成镜中人形的血腥搏杀。
四、最后一剂解咒丹
元旦夜放完千子毽,我看见他蜷缩在屋檐下的姿势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,尽头处有个佝偻的老太婆举着竹筛——筛底躺着半片药方残页。我冲进厨房翻出老卤缸,把浸泡过蛇胆的药酒灌进他喉咙。他脸色发青时,我这才想起太奶奶生前念叨的那句:“做爰XXXⅩ性生交,是用命根子换来的月月红。”
天亮时,床头的青花瓷罐子里装着廿八枚血朱丹。他离开前塞给我一方绣着双喜字的绸帕,角上绣着我和他的名字——都是用金线刺成的轮廓,空心的部分像两只永不可能合拢的眼睛。我摸着绸帕凹凸不平的质地,想起他第一次吻我时说的:“这咒法像极了劣质豆腐,看着结实,捏着就碎。”
春雷响起的那天,我站在空荡荡的房檐下。雨水打湿的青石板上,浮着半枚破碎的银面具。隔壁的哭喊声依旧断断续续传来,却不再是那对夫妻。街上闪过戴银面人的陌生人时,我会想起他临别时说过的话:“咒术改写的人性,就像残雪覆盖的河道,等春天融冰时,水面那层微光才是真相。”
我摸着胸口新生的伤疤,那是最后一个满月时他留下的。伤口愈合得异常平整,像有人用金刚钻打磨过。街角风铃叮当声响,青花瓷罐里捣药声随着风卷进窗棂,和着雨声奏出诡异的韵调。我将老卤缸里的药酒兑进茶盏,烫着唇灌下去,苦味倒映出他曾说的那句话:“这世界上最危险的事,不是和鬼魂做爰XXXⅩ性生交,而是你以为自己永远能赢过鬼魂的脾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