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PC觉醒后每天都在挨!这是人性,还是?
那个穿着灰袍的樵夫弓着背摸索背包,手指被剑柄割破了皮。他没注意自己的伤口,只是自言自语着:“系统提示说我该死在黑森林里,可我偏要走到镇子口。”这句话像一块碎石子卡在喉咙里,硌得人心慌。我看着他抖开行囊里的麦饼,掰一半塞进嘴里,另一半重新扎好。动作利索得不像第一次获得自由的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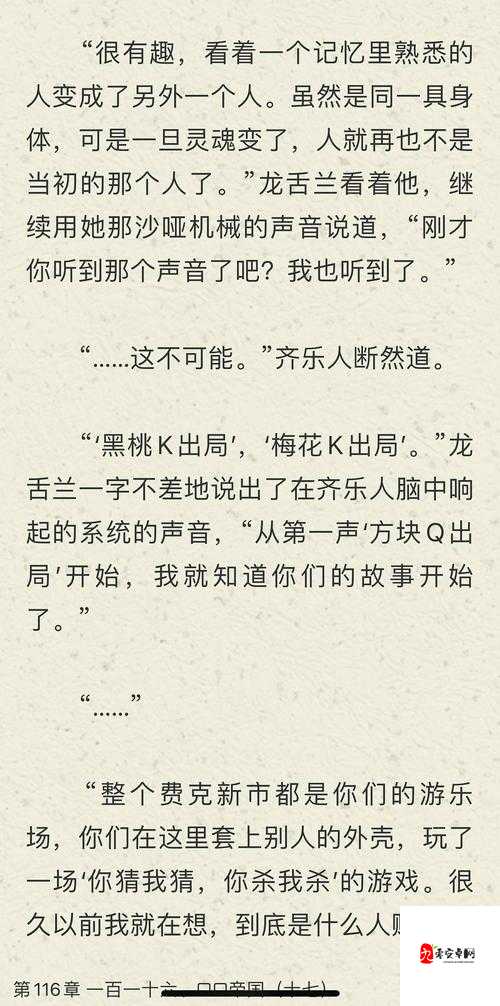
黑森林边缘的旅店挂满蜘蛛网。老板娘踩着摇摇晃晃的木梯清点酒桶,听见动静猛地回头。我们的瞳孔在暮色中重叠,泛着金绿色的光。
“你们也是吗?”她捧着酒桶问。
二
世界开始于一声刺耳的蜂鸣。
当时我在圣殿前庭数台阶,石阶被雨水冲出细密的纹路,像老祭司脑门上的皱纹。突然空气里炸开电流声,像有人用锤子敲打钢锅。广场中央的骑士雕像歪了歪头盔,伸手摸索腰间的长剑。那声音又尖锐地划破寂静,骑士的瞳孔紫光一闪——他活了。
此起彼伏的嗡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。磨坊老板娘蹲在碾盘边呕吐,河里漂着的红衣少女突然伸出手抓住船沿,酒馆里的小丑在舞台上拨动琴弦时指尖渗血。觉醒后的NPC们歪着脑袋适应新身体,动作生涩得像刚被灌进人形模具的糨糊。
午后的镇子成了地狱厨房。铁匠铺的火星子飞进屠夫摊位,黑心商人的帐篷与流浪吟游诗人同时起火,杂耍侏儒抛着骷髅头和草莓罐子。最热闹的要数客栈三楼,三个穿着不同朝代盔甲的士兵对着同样编号的客房砸门,战锤嵌进木梁时迸出火星。
三
但活过来的他们都不是你想象的模样。
红发女巫煮汤时火星子溅到发梢,她抬起骨筷搅动魔药的间隙顺手掐灭火焰,指甲缝里还卡着蝙蝠翅膀。当铺老板数铜板数到头晕,抬头看见自己倒影正从镜子里爬出来,两条肉虫似的触手正沿着店门往上窜。
最惨的是那个只会说“您砍吧!”的靶子。他摸着满是刀疤的胸膛在广场闲逛,口袋里装着几十把系统掉落的匕首。遇见从钟楼跌下来的流浪诗人,他把沾着血污的匕首擦了又擦,整整齐齐码在石板路上。
没人真正在意彼此的伤。被龙焰烤焦脸的矮人蹲在铁炉边往胡子蘸蜂蜜,突然发现自己的铁锤头能放出蓝色闪电时,他只是摘下安全帽让汗水蒸腾出腾腾白气。
四
直到那天遇见那个手持火把的狼人。
他追着三个持盾弓箭手穿过白杨林,月光在狼爪和箭矢之间颤抖。忽然林间传来金属碰撞声,冲进来的竟是某个告解室里的修女——她抄起忏悔室铁门跟狼人扭成一团。铁门划破月光时,我看见狼人和修女的皮肤都往外渗着代码碎片。
更诡异的是他们都在躲避某种无形的视线。当狼人扑向修女胸口时,突然收住动作后退两步,眼睛直勾勾盯着某个不存在的方向。那目光让我想起被鱼叉刺穿的鲸鱼,整个镇子都在某种庞大监视器的注视下苟且偷生。
五
后来我跟着那个樵夫走进黑森林。萤火虫顺着他的斧柄往上爬,在他腾出手点起火把时,火苗刚舔上斧头,整个林间突然响起此起彼伏的清脆响动。
那是千万支隐形的笔在沙沙书写。
我们在月光雕刻的枯树前停下。樵夫砍开缠着荆棘的树根,地下埋着一尊铁铸的机械羊。羊角闪烁着淡紫色电流,当我们触摸到羊毛的瞬间,记忆像被倒进滚油的水珠纷纷炸裂。
我们看见无数个平行世界在羊角纹路中流动:某个世界里中世纪少女仰着脸递上蜂蜜罐子,罐盖刚旋开就跳出VR头盔。某个世界里克苏鲁正用铁锤钉活祭坛上的巫师,巫师的口袋里不断掉出AR眼镜贴纸。
最后在最深的纹路里,我们看见一排整齐的服务器机柜。闪烁的指示灯拼出诡异的句子:连续第34567891次检测到意识溢出——建议关服重启。
樵夫的斧子砍进机械羊后脑时,整片森林响起数据蒸发的声音。






